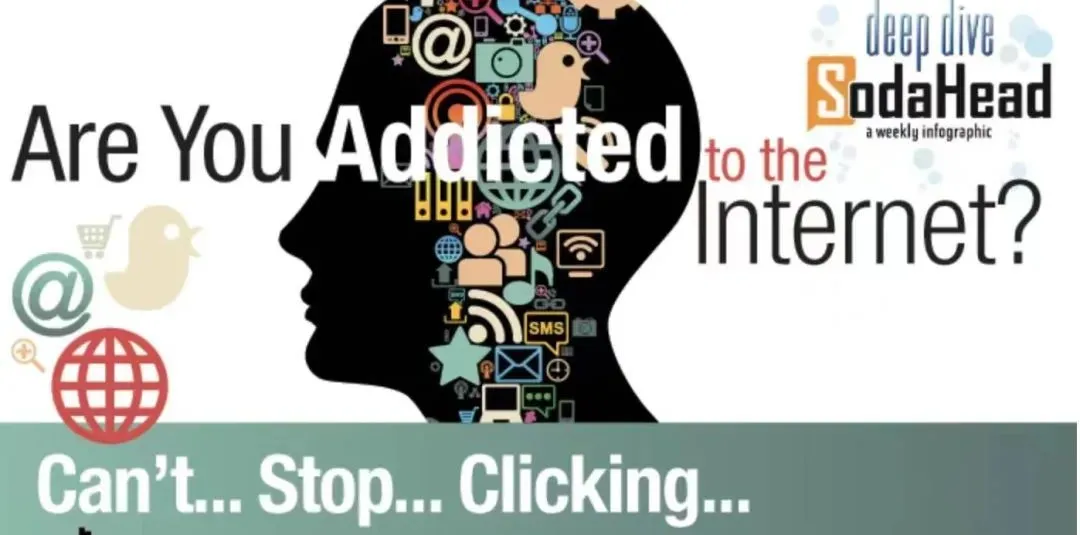到目前为止,我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网民使用手机的比例超过99%。然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问题也层出不穷。很多网民连续熬夜沉迷小说,动辄抖音、微博刷屏,疯狂游戏甚至不顾吃喝等生理需求,也几乎没有网络之外的社交活动……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由于保持社交距离和远程工作的需要,互联网接触和使用量急剧增加,认识并评估网瘾行为的危害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心理学家布兰德教授(Matthias Brand)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了网络成瘾的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网络成瘾对大脑的影响与成瘾药物相似,而且在大脑成瘾路径中,自我控制(self-control)对于是否上瘾有关键影响。
网瘾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世卫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ICD-11)第11次修订版中,特意突出了两类网瘾问题,即赌博(Gambling)和游戏成瘾(Gaming Disorders)。另外,有问题的色情、购物、社交网络使用等在线行为被认定为其他网瘾问题。ICD-11对网瘾的关注不是偶然的。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有高达3%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患有游戏成瘾,约7%的人群患有未明确的网瘾问题,游戏成瘾人群中年轻人和男性居多。
那如何判断网络成瘾是否存在呢?文章指出,如果上网行为导致忽视自身专业职责、放弃个人兴趣爱好或休闲活动、危害社会关系等负面后果,那大致可以被认为是网上成瘾了。互联网的使用可分为功能性提升使用(functional-enriching usage)和有问题的成瘾性使用(problematic-addictive usage),但如何判别还需要更深理解各种弹性因素和风险因素。
网络成瘾APP的共同点
很多人都对APP(互联网应用程序)爱不释手。布兰德教授在研究中详细阐述了这些APP的共同点,即它们都运用了奖励机制和救济机制。关于奖励机制,首先我们要理解人类进化的先决条件,即事关人类生存的行为,比如性、获得物品、社会交往等。APP的奖励机制就是充分利用人类的这些本能,其提供服务和产品不仅为用户带来愉悦感受,还以此强化用户的使用行为。APP的救济机制是指帮助用户逃避负面情绪,像喝酒和玩游戏一样缓解压力,并在此过程中会带来负面强化效果。这些机制可以解释特定的APP会比其他APP更容易让用户上瘾,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用户会上瘾,而大多数用户不会,所以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网瘾行为的内在形成机制。
网瘾行为的驱动路径
”以往关于网瘾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物质使用的理论和发现,包括与自我控制减弱相关的研究以及从奖励性行为向强迫性行为转变的潜在假设。在本文中,布兰德教授提出,网络上瘾存在两条内在驱动路径,即“感觉更好”(feels better)和“必须做”(must do)的路径(见下图)。
“感觉更好”的路径包括积极情绪(比如感到愉悦、获得奖励)和消极情绪(比如缓解压力和负面情绪)的强化体验,并在后期涉及腹侧纹状体(伏隔核)和背侧纹状体。“必须做”的路径可能发生在网络成瘾的后期,主要包括习惯性行为(即对刺激物产生自动反应),尤其是强迫性行为,涉及背侧纹状体(壳核和尾状核)。强迫性行为描述了一种持续性的不适行为,尽管意识到其负面后果但仍然不会停止。就如同年轻人熬夜玩手机,即使困倦不已也还是无意识强迫自己继续刷屏。
在这个模型中,还有一个“立即停止”(stop now)机制,它源自自我控制的努力,主要涉及前额叶背外侧皮质,可以调节成瘾的两条路径。模型的主要假设就是上网成瘾的个体在驱动路径和自我控制之间存在失衡。
网瘾与“嗑药”相似?
”不仅如此,在近些年的神经影像学和神经认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网络成瘾中的提示反应(cue reactivity)与行为渴望(craving)存在行为与神经层面的关联,同时证实腹侧和背侧纹状体在网瘾驱动路径中均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对网瘾人群的认知功能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es)后,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与前额叶皮质相关的决策及其他执行功能减弱的证据。这与另外一项针对网瘾人群的脑结构变化的元分析一致,该研究显示网瘾人群的前额叶背外侧皮质、前扣带回和辅助运动区的灰质体积都减少了。前额叶作为人的大脑发育最晚的部分,主要负责情绪、认知等社交功能。如果在青少年时期过多地沉迷于只有声音、视频等信息的虚拟交流,那么缺失气味、眼神、接触等非语言信息的成长环境,将使脑功能持续损害,社交能力也表现迟缓甚至发展低下。现有的研究结果初步支持了网络成瘾和物质成瘾之间的相似性。但在布兰德教授看来,仅仅知道网瘾与药瘾之间存在关联还远远不够。在理解网络成瘾心理和神经生物学机制方面,我们还面临脆弱性、因果性和特殊性等方面的研究挑战。
关于网瘾脆弱性的研究
关于潜在的脆弱性,已有研究发现网瘾行为具有遗传倾向,并识别出了与多巴胺受体、血清素转运体、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相关基因的多态性现象。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潜在脆弱性因素,包括消极的童年经历、不安全感导致的过度依赖、个性特征(如冲动性)、情绪管理能力的匮乏、抗压能力差、社会支持的缺乏、有问题的原生家庭等。但这些风险因素并不是网瘾行为所特有的,它们与吸毒、抑郁、焦虑、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等都有关。布兰德教授因此指出,网瘾研究应确定更具体的脆弱性因素。为了区分正常和非正常使用互联网的行为,还可以探讨哪些风险因素和恢复力因素决定了使用特定APP的奖励和救济机制。
关于网瘾因果性的研究
”另一大挑战是探讨与网络成瘾相关的大脑机制所包含的因果性问题,特别是前文提到的驱动路径和自我控制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相关报道显示,就游戏成瘾和其他成瘾行为而言,与其相关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可能来自成瘾时所发生的神经可塑性变化,但也可能出现在更早时候。减少的前额叶功能可能是一个缺陷,当边缘回路在成瘾过程中变得更强时,前额叶功能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少。由于目前大多数研究只是比较了有无网络成瘾行为的相关个体,关于因果性的认知有限,因此还需要前瞻性设计和相关对比研究,从而发现成瘾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和心理社会脆弱性以及因果关系。
关于网瘾特异性的研究
”与其他成瘾行为相比,网瘾行为中有哪些特定的神经生物学和心理机制?布兰德教授对此指出,与成瘾性物质不同,APP本身能够适应用户的使用模式并激发个人强化体验。此时的APP会进一步强化“感觉更好”和“必须做”两条驱动路径,并潜在凌驾于自我控制之上。深入分析APP的特定功能以及这些功能如何影响用户的动机(例如发现、归属感、物质主义价值观),可以提升我们对上网成瘾因果性和特殊性的理解。进行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网瘾行为是否是特立独行的(如游戏成瘾),还是一组有问题的网络使用行为,或者是某种网瘾类型的变异(如有问题的色情制品作为网瘾强迫性行为的变体)。在布兰德教授看来,网络上瘾不是简单的个人的选择,而是难以做出有利的选择或者难以恰当调节奖励行为导致的。有鉴于此,他呼吁优化网瘾这种新兴心理健康状况的预防和治疗,在全球的研究机构间开展合作,共同进行大规模的多方法的纵向研究;尤其需要关注当今时代的社会动荡(例如新冠大流行以来互联网使用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更多的人网络成瘾,以及这种影响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文献来源:Matthias Brand (2022). Can Internet use become addictive? Science 376(6595):798-799.